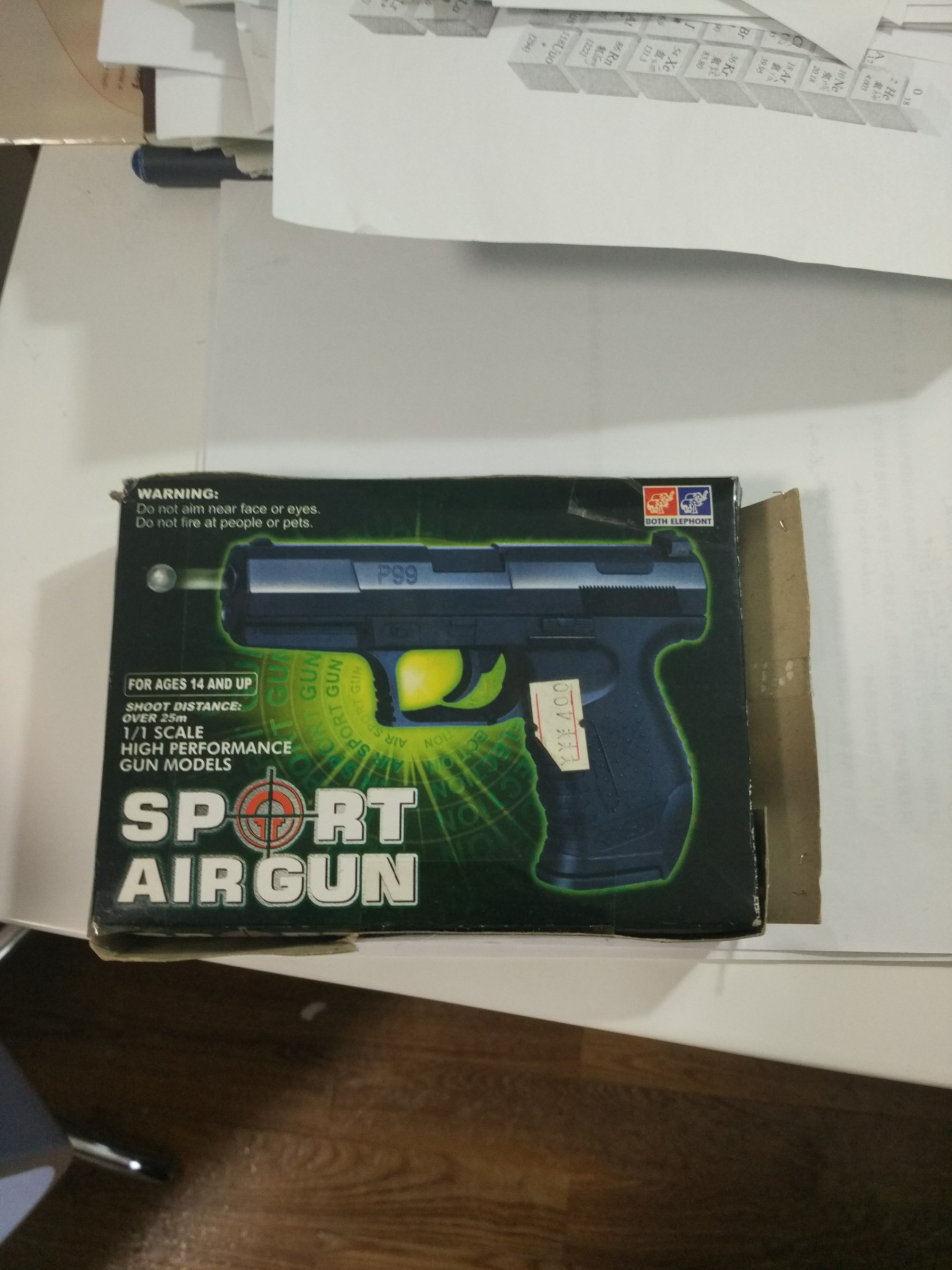足球报作为南方的报纸,较国内其他地区的报刊商业化更超前一些,而且由于背靠香港,很多广告与香港产品有关,这样就为足球报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,使得足球报在国内专业体育刊物中属于龙头地位。
在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,足球报派专门记者前去采访,这在国内算是少见的。其后几年,足球报的记者廖德营新瓶装旧酒,凭借着世界杯上的照片,在国内体育摄影比赛中多次获奖。而墨西哥世界杯专刊也是我们第一次从足球报邮购产品,算是世界足球知识的启蒙读物。
从87年开始,足球报一直是家里每期必买的报刊,上大学期间,学校附近报纸卖完,曾坐车跑到大观园去买。
但就是大学期间,足球报似乎开始不思进取,看重所谓名嘴评论,而轻现场报道,尤其是越来越受关注的国际足球,大篇大篇地转载新华社通讯,而这时候体坛周报开始迎头赶上,吸引球迷的很大一个看点的就是欧洲五大联赛报道,重头戏是如日中天的意甲联赛的张慧德专栏,而他本来是足球报的座上客。
使我最终放弃足球报转买体坛,是一次世界杯前足球报报道意大利国家队名单时,竟然将尤文图斯翻译为青年队,国际米兰翻译为国家队。这哪像一家专业报纸做的事。
进入网络时代,报纸基本不再买了。但同当年报纸一样,网络媒体同样也应是内容为王,单纯靠那些夸张标题博眼球的剪刀文注水文撑场面,终不长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