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末两天在家,时间宽裕,古籍点校进程出乎意料的快。重头戏第四卷点校完成后,第五卷文字录入也完成了。
与寄青霞馆系列打乱顺序不同,本次整理的古籍共24卷,是按照棋手汇总分卷。前两卷是眉山四杰对弈荟萃,第三卷为周懒予个人专辑,第四卷则是重中之重的黄龙士对局集。
昨天晚上熬了一会夜,把黄龙士对子部分76局完成了。进程顺利,主要是此前公众号整理过黄龙士全集,准备工作最为充分。
完成第四卷后,按照棋手的出生年月顺序,预计第五卷是徐星友的棋谱专辑。但意外的是,83局棋谱中,徐星友的棋谱只占了一半多一点,后面则是其后辈棋手的零散对局。
至于徐程十局,应该放在后面程兰如的对局集中。也许徐星友在作者心目中,是低于四大家中的程兰如、梁魏今的。
分类: 纹枰论道
弈墨不入法眼
昨天整理古籍到第三卷,本卷的主角换作周懒予,称得上是周懒予的专辑。
棋谱主要来自《兼山堂弈谱》与《周懒予围棋谱》,后者的棋评中,不少是引用的《弈墨》。
对照之前整理的《弈墨》资料,发现虽然相比《弈悟》与《不古编》流水账般的棋评,《弈墨》的棋评已经称得上精炼,而本古籍的棋评抄录又进一步进行了简化。
这应该不是作者偷懒,否则《弈悟》的注水棋评更可以删减,这说明《弈墨》在清代的版本有多个。
另外一个大疑问就是,这个古籍中的棋谱大多数也被收录到寄青霞馆系列,而偏偏《弈墨》的棋谱一局也没有收录。
之前我认为这是寄青霞馆的编撰者看不上《弈墨》,看来猜测是对的。
古籍点校,难关已过
本次回家的一大工作,是想突击完成部分古籍文献的点校,因为原先购买的相关古籍书籍都在家里书架上。
开始整理了发现,原先那些书其实作用不大,主要是现在整理的大部头是手工毛笔抄写,清晰度非原先的刻本所能比拟。既然不存在字迹难以辨别问题,也就没有必要参考原先的刻本点校资料,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。
晚上整理完24卷本的前两卷,最为艰巨的任务已经完成。这2卷中有《眉山墅隐》的全部60局,半数以上的《兼山堂弈谱》棋局,大部分的《不古编》流水账,后续工作难度与强度要小多了 。
第三卷,黄龙士要登场了。
读书人的颜面
最近没有更新自己的公众号,主要是因为忙于点校古谱。
原先在公众号号也发布了不少文章,但基本属于兴趣所致,随性而为,发了也就发了,错了也就错了。
而现在点校开始后,真的不敢再有马虎二字。这跟稿酬没有关系,算是读书人的一点颜面吧。
好歹算得上是读书人吧。
今天整理到《眉山墅隐》,回看对照原先的文章,真是汗颜。
希望完成本次工作后,能换一种方式更好整理古谱吧。
《血泪篇》开篇杂谈:katago的PDA调整
与《弈墨》不同,《血泪篇》中的对局属于让子棋,在使用AI犬分析前,我一直纠结是否要调整PDA。
PDA是katago配置文件选项playoutDoublingAdvantage的缩写,网上也被谐音称作“骗到啊”。通过设置PDA值,可以让AI犬知道自己比对手更强或更弱,并相应地进行下棋。通常设置为正值,最高为3.0,用作提高让子棋强度。
在初步分析《血泪篇》的时候,发现即便PDA设置为正值,在布局阶段效果并不明显。只有设为最大值情况下,白棋才会下出一些与实战胜率差距较大的着法,但实际意义并不大,因为三子优势本来就大,而已崭露头角的徐星友也非等闲之辈。
让我彻底放弃调整PDA念头的,是年后跟一位网友的让六子测试棋。那位网友前年曾经输给过katago,但当时的水平,katago在8万maxvisit设定下,已经让不动六子。在调整到PDA的最大值后,AI犬似乎也只是满足于少数几目而已,而不是追求胜利。
这应该就是好强争胜的人类,与无情绪化AI的区别。而这也是我赞同陈祖德先生《血泪篇》只是二人从“四子进至三子”阶段的正常对局而已。
同时,现代人在评论黄龙士让子棋技艺时,赞其“极擅让子”,“下让子棋时,却极少大砍大杀,弈得温文尔雅,却如同软刀子割肉,下手并未出什么大恶手,不知不觉中便已败落”。
这也正是《血泪篇》十局黄龙士棋艺的最好写照。
所以,在AI观古谱的《血泪篇》系列中,我放弃了对PDA的调整。
再购《围棋词典》
下午在外面忙的时候,收到一个丰巢的短信,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买了什么。
晚上回去打开柜子看到是一个小包,才想起是自己从孔网上买的《围棋词典》。
三年前曾经买过一本,去年做的围棋古谱时也时时翻看这本书作为参考。进京之前还曾犹豫要不要把书带上,后来一想,还不知待多久,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,打不了再买一本就是了。
前几天跟ChatGPT交流的时候,问起围棋名局的标准。ChatGPT回答的依然是一二三四,有条有理,但我实在不敢苟同。
于是又想起买一本《围棋词典》吧。书不贵,才七块钱,快递费却要10元,这年代,书真是不值钱啊。
书到手打开,说是八成新,却要好于我原先那本,打开扉页,看到原先没有注意到,除了编者,还有校阅人。而校阅之一曹志林先生,也刚刚去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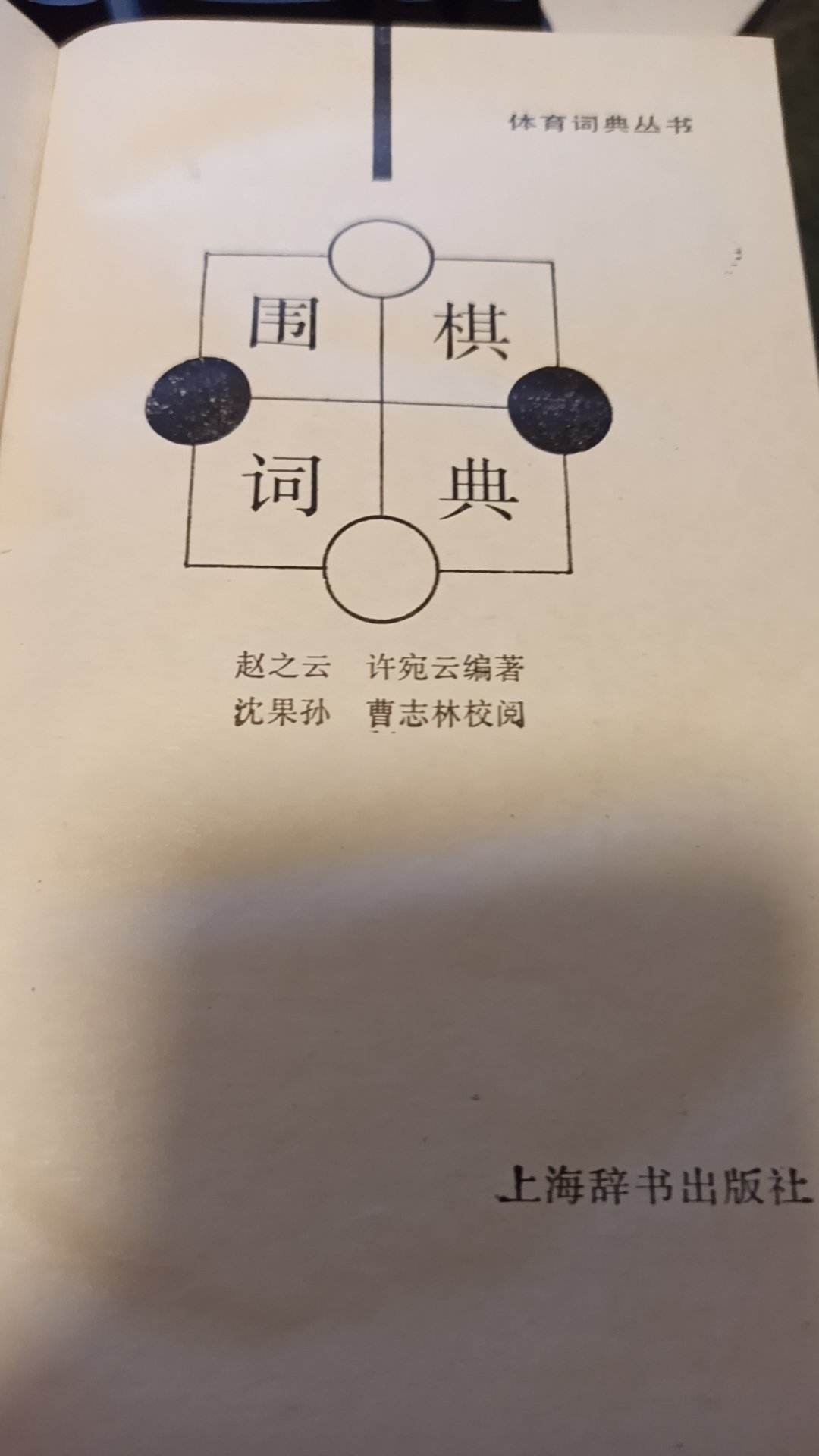
让子棋让人失望的18B权重
去年感觉到自己阳的时候挺突然的,当时正在网上跟一个网友测试katago让六子棋,突然之间感觉头疼,脑子几乎空白,屏幕都看不清楚了。
那之后一脑子感觉昏昏的,集中精力时间长一些还会有刺痛感。
昨天晚上又与那个网友约定进行让子棋测试。可能为了保证系统稳定,减少了AI信息的返回量的缘故,动脑少了,躺下后脑子没有昏沉沉的感觉,反而清醒的很。
不过测试棋中,目前风头最劲的18B权重实在有失面子。不止是我,被让子方也怀疑是自己水平提高了,还是AI出了问题。即便将pda设为最高,18B依然是斤斤计较官子的大小,可以说是按部就班地输掉对局,或者说,他根本就没想赢。
我们均不甘心,又换成最新60B权重对战一局,结果对局进程幡然一新,从角部开始缠斗,一直纠缠到官子。虽然因为机器配置低,计算量不高而告负,但依然有取胜的希望。
估计现在一直没有更新的18B权重,如网上流传那样,是为了比赛而特训的权重,可谓棋风全面稳健,官子滴水不漏,颇有小林光一之风。
而到了让子棋,必须强力攻击,就非其所长了。
贴目制的时代顺应者高川格
这几天每天看一期邮购的《围棋天地》,原先连载的《世界冠军·回忆杀》进入一冠群时代后,估计成色不足半途而止,改连载《百年棋士》了。
今天看的一期的棋士,是流水不争先的高川格。文中写到:高川的绝技是善于运用形势判断和贴目技巧。
如果绝技有优次,那这段文字中高川绝技项要反过来,那应该是在贴目制下的形势判断。
我一直有种感觉,高川是围棋进入贴目制,最早适应这种赛制的棋手。他的本因坊九连霸,是他及时顺应时代潮流的战果。
与之相反的,正是昭和棋圣吴清源,那无贴目十番棋的王者。
而适应慢的,则是剃刀坂田荣男。
随着另一贴目制名人战的创办,围棋,或者说竞技围棋全面进入贴目制时代,高川的时代也就结束了。而他在名人战击败林海峰,也是他最后的荣光。
爱犬观大赛:由农心杯柁嘉熹与姜东润无胜负局看AI对规则理解
还算恰当的处理意见
从个人角度来看,虽然之前对棋协在疫情期间无作为深感痛恶,但就事论事,其对杨鼎新事件的处理是恰当的。
杨鼎新提出二十番棋挑战后,网上很多评论认为李轩豪的沉默,是怯懦,是心虚。但他们显然忽视,或者完全不知道了一件事,那就是中国棋手参加的所有比赛,必须由棋协或者说中国棋院同意并参与。
李轩豪的沉默,无疑是明智的。
相比李轩豪,杨鼎新的行为就更显得冲动而无脑。同时他还忽略了自己的身份,除了是中国棋协注册的棋手,他还是享受着国手福利的国家队棋手。
享受权利,就要承担义务。
而杨鼎新还有那些帮其鼓噪的国手,就是在滥用他们的权利。
此外,处理意见着重提到杨鼎新在朋友圈发文,这已经对事件的定性降格。
只是不知道在禁赛的半年时间内,杨鼎新的训练,是继续选择自己以往的网棋,还是会选择AI训练,自己曾经不屑的李轩豪的训练方式。
希望是后一种。